- 文学
- 小说
- 艺术
- 古籍善本(国学)
- 动漫绘本
- 生活
- 励志
- 社科
- 经管
- 文化
- 教育
- 幼儿读物
- 体育
- 外语
- 历史
- 地理
- 计算机
- 科技
- 生物
- 医学
- 农林
- 工业
- 综合
- 进口原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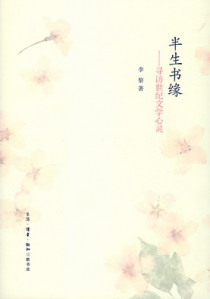
-
作为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到大陆走访的旅美作家,作者李黎女士和老一辈作家、学者的交往结缘的机会,乃是他人企望不及的。当年她在范用先生的引导下,一一拜访过茅盾、丁玲、巴金、沈从文、黄永玉、艾青、钱锺书、杨绛...
作为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到大陆走访的旅美作家,作者李黎女士和老一辈作家、学者的交往结缘的机会,乃是他人企望不及的。当年她在范用先生的引导下,一一拜访过茅盾、丁玲、巴金、沈从文、黄永玉、艾青、钱锺书、杨绛、李子云……宝岛台湾的殷海光、陈映真,也是作者的文学启蒙者和故友。因此,《半生书缘》以这十二位人物为中心,用题记和图片结构各个时期记述他们的文字。作者整理成书,发现“倏忽已过半生”、“人书俱将老去”,但犹盼这些关于人与书、情与缘的篇章,能够成为“一个文学和文化的历史见证,一个20世纪民族书写的侧影素描”。
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 刘心武
长河侧影——《半生书缘》自序
茅盾
去冬见茅盾
乌镇倒影
茅盾的题字
巴金
巴金先生谈过去现在、将来
【附录】“中国的良心
重访巴金的家
沈从文
夏日北京:沈从文
沈从文的长河
命运之杯
从文让人
【附录】人间风景——读黄永玉
《太阳下的风景》及其他
丁玲
“今生辙”——访丁玲
在延安想起丁玲
“五四”女子
艾青
北方的吹号者
钱锺书﹐杨绛
一封“迟到”多年的信
给方鸿渐博士的一封信
读钱锺书《槐聚诗存》
又见杨绛
背影
一个人和三个人
百年才情——岁寒访杨绛
范用
半生书缘——记范用
【附录】双槐树
李子云
昨日风景——怀念李子云
殷海光
长巷深深
陈映真
映真永善
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
李黎《半生书缘》序
刘心武
北宋大儒张横渠发出宏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等一般读书人,难以承担如此大任,但在“横渠四愿”的鼓舞下,或许也能以绵薄之力,多少做点沾边的事。
比如,“为往圣继绝学”,一般读书人,系统地承继“绝学”,很难。但是,对“绝学”心存尊敬,以点滴之力,融汇进将割断的学问重续的时代工程中,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往圣”的“学问”之所以会被遮蔽、践踏、湮灭,其中最主要的,当属政治因素。在宏大的“往圣绝学”中,我们现在只取小小一瓢,即中国现代文学,来观察一下。由于1949年形成的新格局,在海峡那边岛上,上世纪前半叶的现代左翼作家的作品,一度被遮蔽、禁制,不仅鲁迅的文章读者读不到,举凡茅盾、巴金、丁玲、艾青、沈从文……的作品,也成禁书。海峡另一边呢,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不断革命”,跑到岛上或异域的作家作品,也多被遮蔽、禁制,有的如胡适,对于一般年轻读者来说,只知他是个反动派,被猛烈批判,他的文字,只在大批判文章中被零星引用以为靶环,想看到他作品的完整面目,极难。再如梁实秋,他的大名是让人知道的,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是撕不下的标签,至于他写有《雅舍小品》,则不仅看不到,甚至连信息也不给。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的作家,沈从文不仅不再写小说,连作家的身份也被褫夺,只好去故纸堆里讨生活,研究古代服饰;丁玲、艾青、吴祖光……等陆续被打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巴金、曹禺头十七年还算太平,到了“文革”,也被打倒;钱钟书因为懂多门外语,总算用他一技之长,去参与翻译领袖诗词,但他在1949年以前曾出版过的长篇小说《围城》,在进入改革开放阶段才获重印,那之前的三十来年里,连我这样的“文学青年”,也并不知晓……
上面所提到的诸位现代作家,单个来说,或许有的难称“文圣”,但合起来,应是一个时代的神圣文脉,怎能将其从读者视野中“扫地出门”?
于是出现了一些力图冲破禁制,将切断的文脉接续上的较为年轻的读书人、写作者。李黎即其中一位。她1948年出生不久即被舅舅舅妈带往台湾,在那里长大成人,经历过台湾“戡乱”的威权政治所实施的白色恐怖,其中包括禁读鲁迅及留在大陆的诸作家的书,但年轻的心,首先是好奇,读书本无禁区,奈何钳制至此?没有不透风的墙,你禁的人名书名,总会灌进耳朵里一些,你越不让看,我越想看!好奇心驱使下,就要寻觅,偶得“禁书”,兴奋不已。但那时的台湾实在令人窒息,直到她留学美国,忽然在图书馆里看到书架上大片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作品,惊喜之后,便联翩阅读,阅读之后,就想,有的作者还活在大陆,那么,能否有一天,去往那片祖籍之地,跟他们结识,当面聆教呢?
1979年,李黎来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大陆。邀请她的,是北京三联书店的总经理范用。范用当时起到的作用,就是把被政治震荡切断的文脉,尽力接续起来。当然致力于这项工作的机构和人士还有若干,但北京三联书店和范用,应该说是得风气之先,起步最早,着力最多。李黎那时侯大陆知道她的人不多,范用真是慧眼识明珠,请到这位台湾长大、美国定居的不过三十出头的年轻女子,在北京做报告!范用好比巧妇,李黎仿佛金针,那场演讲,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断线,在新时期中得以接续,穿过时代的针鼻,将海峡两岸、大洋两头,原来破裂的文学衣衫,精心缝补起来,华衫再现,霓裳羽衣……我这样形容,当下的年轻人或会觉得夸张,那是不知那段历史时期所穿越过的隧道,曾是多么阴暗。
凭借范用的举荐,李黎见到了茅盾,她的第一本个人小说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茅盾先生为其题写了书名;后来又有中国作家协会孔罗荪等开明人士的帮助,她在那年和以后几年里,相继见到了丁玲、艾青、沈从文、黄永玉、王世襄、钱钟书和杨绛、吴祖光与新凤霞、丁聪和沈峻,杨宪益和戴乃迭、黄苗子和郁风、冯亦代和黄宗英、黄宗江和阮若珊……当然,她“不薄旧人爱新人”,也很快就结识了刘宾雁、白桦、李子云、张洁……等相对前面所开列的先贤辈分较小的作家,她自己称,其中年龄相对最小的一个,是我。所谓“最小”,是与前面诸位相比,其实我比李黎大六岁,她称我为兄,我是不必谦让的。
说来有趣,于李黎,我是未见其人,先遇其夫。1978年,也是范用先生牵线,给我来电话,说有位台湾去美国定居的薛人望先生,虽是研究细胞学的学者,却又是位文人,读了我1977年11月刊发在《人民文学》杂志的《班主任》,想对我做次采访,建议我解除顾虑,接受采访,畅所欲言。我接受薛人望采访后,他将那篇幅很长的采访录署名张华,拿到香港一家杂志刊发了。那次采访中,他就告诉我,不仅他觉得《班主任》是个重要的文本,他那写小说的妻子李黎,也同样赞赏。1979年李黎只身来到北京,我不仅在集体活动中与她见面,更邀她到家里做客,从那以后,我们成为极好的朋友,1987年我第一次访美,就在他们圣迭戈家中小住,1998年我和妻子吕晓歌同游美国,又到他们史坦福大学里的居所住了很多天。
《班主任》不是好小说,但敝帚自珍,它确实是个重要的文本。写它的心思,是觉得“文革”把四个方面的文脉几乎全给切断了: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1949年以前的现代文学、1949年到1966年上半年的当代文学,每个范畴里或许留下零星的作家作品尚允许存在,其余基本上一笔抹杀,这样的文化政策,使得年轻的一代陷于愚昧,因此重呐鲁迅喊过的那一声:救救孩子!这个文本里的那种急于将四个方面被割断的文学重新续接上的内涵,不消说,正与李黎当时内心里那种“冲破桎梏读禁书”的情愫息息相通。这应该是我们一见如故的缘由吧。
李黎当年见过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地位的作家后,来到我跟前,总愿跟我细说端详,有的内容,似不见于她后来的文章。比如她初见艾青,他们言谈甚欢,当中艾老忽然说失陪,去了另一间屋,关上门,移时许久才返回;那时艾老刚落实政策返回北京,暂住在简陋的平房里,李黎推敲,因为没有卫生间,艾老应该是到隔壁屋使用罐罐去了,她很为这样的国宝级诗人不能有好的生活条件而喟叹;她又跟我议论,艾老一侧额头上有个大包,按说很不雅观,但是想到那包里应该有许多的诗思,也就觉得不难看了……
1987年蒋经国宣布结束“戡乱”,开放党禁、报禁,那以后台湾的出版阅读禁区基本上不复存在。大陆也有很多良性的变化。但是李黎所结识的老一辈文学艺术家,许多都仙去了。2012年她又来北京,我们见面时不免扳指逐一清点,硕果仅存者虽有,却陡生夕阳箫鼓之叹。
虽如此,“继绝学”之事,也还可以小处做起。李黎将她多年来这方面的文字,编为《半生书缘》,是对前辈文圣们的致敬,也是对后来的读书人、写作者承继文脉的一种提示。
李白当年写出的诗何等的好,但他不认为自己的诗才是凭空而来的,除了对现实的敏感与想像力的飞扬,对往圣的尊崇,对传统的继承,是他时时难以释怀的,他有多首缅怀早他二百多年的谢眺的诗,其中《谢公亭》是这样写的:
谢亭离别处,风景每生愁。
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
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
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
我以为,李黎的这本散文集,多少有些李白此诗的韵味,不信你看。
2013年1月19日 时逢阴历腊八喝粥后 北京绿叶居中
长河侧影 - 《半生书缘》自序 李黎
写出了童年和家族的回忆录《昨日之河》,接下来整理多年来纪录因文字而结缘的两岸人物的新旧文章,发现结成之书也可以视为一本回忆录 - 我写的是那些位文学人物,记下的其实是我从少年到中年的文学人生之旅,途中记忆的点点滴滴,简牍篇章;其中有些当时就如获至宝,据实以书,但也有存留筴底未曾示人的。
十二位作家、学者、出版家、评论家,其文其人,都曾在我的文学生命里走过,有的驻足指点,有的伫留长谈。他们的话语文字,容貌举止,在我至少一半的人生里留下的涓涓记忆,随着时间汇成了一条荡荡长河。我在印象犹新的当时就用书写记下,更有幸者尚有图片的纪录。在其后的岁月里,当珍贵的记忆再被触及,我还以新的文字补充。所以这本书里既有二三十年前的旧文,也有近年甚至刚写出不久的新文。
十二位里,有十位是大陆的作家学人。以我长在台湾、旅居美国多年的背景来说,他们原应是我最不熟悉的人 - 在台湾成长的五零、六零年代里,许多中国近代现代的作家学者,只要是留在大陆或被贴上“亲共”标签的,他们的名字就成了禁忌,更不用说接触到他们的著作了。甚至即使是台湾的两位,殷海光和陈映真,他们的文字也一度遭到查禁。可是何以这些人会与我结缘半生?说起来竟是一桩憾事造成的机缘。
1970年我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在大学图书馆两层楼之间的一个小房间里发现一书架的中文书,里面竟然有我在台湾看不到的“禁书”!我像补课般急不可待的读着,试图弥补那个错失的文学断层。而那时正值文革,这些作家生死未卜,读时更添一份敬惜之心。当时又适逢海外留学生的“保卫钓鱼台”运动;投入这场“海外五四”的结果是被国府视为“左倾”份子,上了黑名单,十五年不得回家。思乡情切之余,我转而去大陆作文化源流的探索,同时也是为自己的身世寻根。
1977年秋天,我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那时还得先从美国到香港,在罗湖过境进入当时荒凉不毛的深圳,然后北京、上海、大西南走了一遍。那是一次个人的寻根之旅,我见到了骨肉至亲,也写下了情怀感触。后来与文学界联系上了,1979 年去北京在作家协会上做报告,谈台湾与海外文学,同时结识了几位中青年作家。但我当时最挂心的还是硕果仅存的老作家们。多亏出版界前辈范用先生为我引见,从那年起,我像跟时间赛跑一样,赶着求见尚在世间的老作家。那时距离文革结束还不久,资深的文学人士几乎全是浩劫的幸存者,更有文名早已湮没而自嘲为“出土文物”的。我怀着虔敬又有些许惶恐的心情,访问了好些位原以为再也见不到的前辈。这是之前几年我在那间图书馆的小室中,做梦也不敢奢望的机缘。
就是这样,我一位一位的求见,几乎都没有遭到拒绝。有的赶上见到他最后的夕照余晖,如茅盾;有的结为朋友,一同度过悲欣交集的八零年代、变化巨大的九零年代,甚至还有更久的。
大陆的十位:茅盾,丁玲,巴金,沈从文(附带黄永玉),艾青,钱锺书,杨绛,刘宾雁,范用,李子云……每位至少有一篇、或新旧数篇来记述;此外还有许多文中提及但没有专文写出的人物,我也非常珍惜与他们的结识交往,书中选用的照片里他们的影像,是那段遥远岁月的念想。
当然,台湾的陈映真和他的那辈“文学季刊”的朋友,都是我少年时代文学的启蒙者,对他们我始终深深感念。而重访殷海光温州街故居,就会想起也曾住温州街巷子里教授过我的师长学者,那些温煦的记忆伴随我从青年岁月至今 。
所以,这本书写的并不止这十二位,其实远远还有更多。
逐篇写完题记之后,才悚然发现:每一位书中人,在他们各自生活的海峡的两边,都遭遇过来自他们自己政府的压制迫害,甚至牢狱禁锢 。是巧合吗?还是我不自觉的选择?是因为他们的年龄,正逢上了那个动荡的年代、那段酷痛的历史?显然,他们是中国历史的映照,一群知识分子的范本。 尤其是,但凡有理想、有才华、有风骨的写作者,身处那个时代,无论在海峡的哪一边,都无法逃脱政治的涡漩吧。
为了比对时代背景,我检视书中人物的生年,茅盾是唯一十九世纪出生的(1896),更多的出生在上世纪初,而成长于“五四”年代。最“年轻”的是陈映真,生于光复前的台湾,1937,正是卢沟桥事变、艰苦的抗日战争开始那年。也就是说,他们无论生长在中国的哪一处,从1930到1970甚至80年代,作为一个有理想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难免经历了那段历史为他们铺排的命运。
所以,我所见到、记得、写下的,不仅只是对我的文学生命有过深远影响的人物,更是一个文学和文化的历史见证,一个二十世纪国族书写的侧影素描。可是到了廿一世纪,今天的读者,有多少还熟悉这些人的文字,甚至名字呢?然而,只要是一个阅读者,只要还在阅读,纵使从来不曾直接阅读他们,我敢相信,也无可避免的经由他们滋润和影响过的文字,间接领受了这些文字之中其人和其文的传承。临河就水,虽已望不见河源,也该知道源头来自的方向。
书中的几十张图片多半是旧照,我几乎都能清楚记得拍摄时的情景与心境。那一刻的时光就停留在快门按下的剎那;也有的在其后三十年间还在延续,陆续有了更新的照片,带出逐渐变化的容颜,见证了时光的流逝 - 他们的,当然也有我自己的。我何其有幸得以亲眼目睹历史,当时激动心情之下作出的记录,容待日后沈淀定格。今日整理成书,倏忽已过半生。人书俱将老去,唯愿文字长存,记忆之河长流。
(2013年春,美国加州斯坦福)
夏日北京:沈从文
中国小说里,有两段令我心醉神驰的绝美意象:一是红楼梦里宝玉身披大红猩猩毡,消失在白茫茫大雪地上;一是沈从文的〈边城〉,翠翠在睡梦中听老二的山歌,灵魂文月光下美丽的歌声浮起来,飘过白塔,飘到悬崖半腰上摘了一把虎耳草。
然而沈从文说:「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是因为美总在消逝吗?在去看他的路上,我惘惘地想着这些事。他家在崇文门外的公寓高楼──当然已经不是早先逼仄的一间小屋、两里地外又一间住着妻子那样的境况了。他的表侄、画家黄永玉在那篇写他的〈太阳下的风景〉里,称那两里遥的居处为「飞地」。读了那些生活记述,觉得《中国服装史》(出版时叫《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写出来是个奇迹──沈从文本来也是个奇迹。
门上贴着不见访客的字条。可见访客一直还是有,虽然沈先生自从中风后行动说话都不便利了。近两三年大陆「寻根文学」风起云涌,而其健将们几乎全尊奉沈从文的作品是他们最早的源流。沈从文笔下的世界有湘西的山乡与河流、牧笛与船歌悠扬的呼唤、善良淳朴的村民在漫漫岁月中的哀乐生息、巫楚文化的神奇瑰丽……但并不仅止是这些。他作品中的世界便是中国,淡淡笔墨后面有浓烈的哀愁和美丽,一条古老河流般的包容、叹息和生命力。因而文学上他虽然休笔四十 年,依然没有被遗忘;而且正是通过了时间和其它的考验,才愈见其妩媚与深远 。
八十五岁的老先生端端正正坐在客厅中央的一张藤椅上。夫人张兆和依然娇小清秀,说话很快,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沈老也笑,但是──唉,在这次中风之前, 他是个最好看的老先生,脸上永远有一朵飘忽可爱的微笑;而现在,不装假牙的嘴笑起来像在做另外一种相反的表情。我才明白为什么有个朋友一去看见他就流眼泪。我把台湾出的一本沈从文专卷杂志给他们,沈夫人说他们已有了,但很高兴能有多一本。给他捎一盒西洋参,还不知合不合适,沈夫人已连声说这个好、 用得着,他总得要吃这个,都是托妹妹张充和买的。
來京之前便有台湾和美国的朋友托我向他致崇敬之意,我照述了。他笑──像苦笑,咕哝了一句话,意思是:后来多少年都没写了。我说:不能写自己想写的就不写,最好。这样就不会有悔作。
谈到小说〈萧萧〉改编成的电影「湘女萧萧」,沈夫人看过,因而有些意见。我说那电影已不是原来的萧萧了,更不是沈从文。又记得沈老在一篇访问中说过: 他觉得〈贵生〉那篇比较适合改编成电影;我便问他们可知道〈贵生〉其实早已被改编成了电影?他俩竟不知道。于是我从五十年代中叶林黛严俊演的「翠翠」大受欢迎开始,讲到不久便再接再厉原班人马拍了下一部「金凤」,便是改编自〈贵生〉的,不过没有提原作沈从文,而且结尾也改了,成了贵生金凤大团圆。我说得高兴,干脆把电影里的插曲也哼给他们听:「咪咪嘛嘛……」金凤赶羊时自诉衷曲的歌;和「光棍苦、光棍光……」金凤贵生打情骂俏的对口歌。顺便也提了「翠翠」里最有名的那首「热烘烘的太阳往上爬呀往上爬,爬上了白塔,照进我们的家;我们家里人两个呀,爷爷爱我,我爱他呀……」真奇怪,小时候学会的歌,一辈子不忘。
沈老笑得像孩子,看看我又看看沈夫人,笑着喃喃说一些话,大约是「我们都不知道哪」一类的意思,夫人似乎非常习惯一边「翻译」他的话一边讲自己的话,融合得天衣无缝。我想到黄永玉这么写他们夫妻俩:「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情况都能驾驶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没有婶婶,很难想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又要严格,又要容忍。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 术家走常人的道路。……」
问他身体,沈夫人絮絮地讲,沈老便很合作地把右胳臂慢慢抬起,又缓缓垂下,告诉我这是他四肢唯一可以活动的部分。为他照像,建议他移坐在窗前,照顾他的男护士扶他起来,两人像角力似地互撑胳臂几秒钟,踉跄一下也就挪移过去了。从镜头里看他,忽然不忍照,真的不忍,在过去那些照片和影片里,他曾是那么好看的老先生……。他忽然发话:「我这样子,像巴金吧──」我一想,老先生们还真的彼此有几分相像。我建议他戴上假牙也许会更像些──更好看些。他固执地拒绝了,说戴上不舒服。我便快快地照了几张,好像拍慢点的话自己就要改变主意了。
沈夫人忙着给我续茶水,因我夸那茶好喝。她说是沈老湘西家乡附近产的,名唤「古丈」。我临走时她细心地盛了一小罐送我。细细的嫩叶有些像碧螺春,泡开来叶子也不大发,回美国家中泡了喝,味道不及在他家喝的好,一定是水不对。那么若在湘西喝该比北京更好了。
站起身来告辞。坐了一个多钟头了,早先电话中约好不多打扰他们的。而我究竟有没有打扰他呢?为什么来看他?他已经不能说什么了,他要说的早说在那几十卷集子里。而且,「真正的痛苦是说不出口的,且往往不愿说。」(又是黄永玉的话。)也不会对我说。那么,是只为了告诉他一句话?他又怎会在意?
我弯下腰握他的手,对着他的眼睛:「在一本选集序言中您说:『我和我的读者 ,都共同将近老去了。』可是,您看,您的读者永远不会老去──」
我快快地走离那间屋子,怕会承受不住自己的激动。他还坐在那里面,在北京的一座高楼上,而哪里是他的湘西?他七十年前离开的凤凰?山城、白塔、神巫、水手、苗女、渡船的姑娘,以及六十几年前把青年的他冻出鼻血来的旧北京城……这一切都已像一桩传奇。
在路对面等公共汽车,看着他住的高楼,估算着他的窗户是哪一扇。下午的斜阳依然热,这城的夏天这样热而冬天那样冷,而当年,二十岁的沈从文来到这里,「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去读那读不完的「一本大书」……
原载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一日《人间》副刊
给方鸿渐博士的一封信
方博士:
首先郑重声明:称您博士绝无嘲讽之意,虽然钱锺书先生在《围城》(注1)中将您这博士学位的来龙去脉不大客气地抖了出来,但这年头──无论是您的三十年代还是我的八十年代──逢人便自动替他加级减岁总是不会错的。
写这封信给您本无打扰之意;我知道您自从被三闾大学解聘,回到上海甚不得意,与尊夫人孙柔嘉女士亦不和睦;内忧外患,加上国事蜩螗,不会有心情欢迎陌生人的来信。可是近年来我们这儿很流行写公开信,给活人给死人给子虚乌有人都行,为政治为爱情为出胸中怨气皆有。编辑先生催索一封写给书中人的公开信,我一不愿给古人二不愿给洋人写信,想到您阁下时空都不太遥远,音容宛在,便决定写这封信向您请教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我胆敢冒昧提笔,当然是假定您还健在──您若活到今天,算算也是八十出头的高龄了,好在您有幸生为中国人,无论身海峡的哪一岸(这点大家都不得而知,恐怕连钱先生本人也弄不清),都还是「大有为」的年纪,很可以应读者之邀发表高见;就算您已因内外交困而英年早夭(对不起),我们也可以文学笔法起您于地下。总而言之:当您环顾周遭,是否生起过似曾曾相识之感?想当年您很赞同苏小姐引法国谚语「婚姻如围城」的说法──她是说者无心您是听者有意;苏小姐掉书袋时完全没有个人感情,很像张爱玲形容孟烟鹂的话(注2),难怪您始终无法喜欢她──很不幸地,结果您不论身在城里城外,都始终胡里胡涂继而沾沾自喜终以鼻青脸肿。半个世纪过去了,如果您重回三十之身再度涉足情场,当今世界好像也没什么改进,您多半还是落得个鼻青脸肿。不知是这《围城 》理论乃古今中外颠扑不破之定理,还是像您这样的人物注定如此悲剧下场?更 槽的是您的悲剧看在王这种没心肝的读者眼中还是喜剧,可见喜剧悲剧往往是某种人生现象的两面写法罢了。
另外想请教的一点,便是书中半个世纪前的儒林群像,您老今天放眼一望,是否感慨更深了?还是五十年磨下来,您早已见怪不怪,甚至练就一身好功夫,比起褚慎明、曹元朗、高松年、韩学愈、汪处厚等等这帮人更高明了?说实在的,您是个具有那么多种可能性的人,锺书先生早在书中这样写您自己看自己:「有几个死掉的自己埋葬在记忆里,立碑志墓,偶一凭吊……有几个自己,彷佛是路毙的,不去收拾,让它们烂掉化掉,给鸟兽吃掉……」大概正因为您是个具有这样多的可能性的角色,《围城》中的您没有个明白的下场结局;钱先生在书尾只以您家中一座走慢的老钟作象征,写下这段令人低回不已的话:「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合上书的那一刻,才开始为您感到余音般的淡淡悲哀。
其实人们真有兴味的对象人物并不是您,而该是您的文学「父亲」,您的创造者钱锺书先生,当今中国公认的第一号博学才子。钱先生学贯中外古今,青年时偶然的游戏之作「头生」了您(注3),您因他而永垂不朽,令人羡慕。锺书先生皓首穷经的巨作《管锥编》、《谈艺录》能读通的人不多,幸好写过这本《 围城》,才让像我这样没有学问的人也能从另一层面领略钱先生的才情。然而钱夫人杨绛女士在她的小书《记钱锺书与围城》(注4)的「前言」中提到钱先生有一回对一位英国「围城迷」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显然钱先生不喜欢崇拜者因崇拜而骚扰他。幸好八年前我尚未读到这些话,因胡涂而胆大地上门拜见钱氏夫妇──自觉的勇敢与不自觉的勇敢其实是两回事,不幸人们常未能分辨,以致世上平白多了许多勇者──见到这对神仙眷侣时高兴忘形,竟然甘冒「对号入座」的大不韪对杨绛先生说:「您一 定是唐晓芙的模特儿!」
方博士,我只能对您重复赵辛楣的话「好眼力!好眼力!」并且深深明白您注定作为悲剧角色的命运了。
祝 永垂不朽
注释:
1 钱锺书先生的《围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我十多年前初读的是在美国买到的香港盗印本,印刷粗劣错字甚多;记得封面图画是一名穿博士袍的 ,头顶上空飘着文凭和方帽子。现有的珍藏本是一九八○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的版本,扉页有钱先生持赠时亲题的毛笔手迹和印章。台湾如有重印《围城》版本,烦请编辑先生明示。
2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她的白把她和周围的恶劣的东西隔开来了,像病院里的白屏风,可同时,书本上的东西也给隔开了。」
3 作者与笔下「头生子」的关系,西西女士在〈胡子有脸〉一文中阐释甚明,见洪范文学丛书《胡子有脸》。
4 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
──原载一九八八‧十二‧廿一《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映真永善 李黎
这篇文字的大部份写于2006年10月16日,那是得知陈映真在北京「病危」消息之后写下的,但没有完成。提笔当时的心情是为自己留下一段纪录,一段自己极其珍视的人生记忆。其后听说他度过险境,至今在疗护下静养已近三年。近日闻知台北将要举办「陈映真创作五十周年」的文学活动,极感欣慰。思念故人,我取出这篇未曾发表的文字,补缀几处小节,谨以此文遥寄远方的映真 - 永善。
我在网络电子报上读到你病危的消息,每读一句﹑一段﹐从颈子到背脊﹐汗毛一排排一道道一阵阵的耸立。这是真的吗?这次恐怕是真的了。
整整一个月前我们在北京重逢。你被旧病与新伤折磨﹐拄着拐杖,比两年前在台北见到时衰弱了许多许多。短暂的餐聚﹐充满欣喜与悲伤﹐一室的人都要跟你说话﹐你已显得疲倦了,我来不及说甚么﹐餐后轻轻拥别了你 - 你显得那样脆弱﹐似乎深怕重一点就会痛到你伤到你。朝着载你离去的车挥手﹐再挥手,然后我别过头去﹐不要周遭的人看见我控制不住的眼泪。
我深知你也是一个凡人,跟每个凡人一样离开的这天终会来到﹐当然会来到﹐但我还没有准备好 - 我永远不会准备好。我不能想象一个没有mentor的世界。
你可能不知道﹕有过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也是我写作最热切最投入的岁月里﹐当我在写的时候﹐会问自己一个必须诚实回答的问题﹕陈映真会怎样看这篇文章﹖
对于我﹐这是最严格的把关﹕这个问题决定这篇文章是否值得去写出来﹔若写出来了﹐思想和艺术层面是否都过得了关 - 过得了我心目中那位mentor的关。
你并不知道。那严格的标准是我设立的﹐以你之名﹐以你的文章、以你的人品。你从来不曾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你的准则﹐那样高贵的文学和思想的准则﹐原不是为我或为某些人设的。那是为你自己。
唯有因为如此﹐我以此要求自己﹐虽然距离你给自己设下的要求已经低了很多﹑很多。
认识你是因为我的干姐姐,你的淡江同学。1966年吧﹐刚进大学不久的我,跟在她后面,羞怯而兴奋地亲眼看见了我心目中的台湾现代文学的赫赫大名。其实早自中学时代,你的文学已经为我启蒙﹐我熟识你的文字﹐熟识到有些段落甚至可以背诵的地步。我着迷于你的文字魅力,瑰丽而深邃,温暖却又冷嘲,温柔却又残酷。写出这样的小说会是甚么样的一个人?跟在干姐的后面,我见到了这些闪亮在我的启蒙年代的名字﹕陈映真﹐尉天骢﹐黄春明⋯⋯我难以相信这是真的。我甚至跟着你们一道去了罗东黄春明的家玩。在火车上﹐我默默听大家谈笑﹐不敢也没有插嘴的余地。我记得黄春明的妻子Yumi纤长美丽温柔似水;我记得尉天骢清秀的女友﹐喜欢在手心写字﹔可是其它的细节﹐尤其在罗东的那两天做了些什么 - 除了走在黄春明小说中描述过的滨海小公路上,其它竟无多少印象了。我真无法相信记忆可以这样如冰块消融。
却是清楚的记得唯有你总是严肃的﹐在火车厢里远远看着你﹐偶然飘来你低沉的bass般好听的声音。我不敢上前﹐更不敢开口说话。你从未主动跟我说过话。你太遥远太高了﹐那一篇一篇打开我少年的眼睛和世界的小说﹐竟是这个人写的啊﹐我告诉自己。见到你只觉得更远更高﹐来自一个我无可能及的世界。我又欣喜又有些悲伤 - 你的眼睛根本看不见我。
你们在看书﹐看许多我仅只闻其名的书﹐禁书。在干姐房里见到鲁迅的书﹐几乎是神秘到神圣的﹐她用不无炫耀的语气说﹕陈永善借给我看的。还有陈永善写给她的信。(所以其实我早就见过你那笔从容而收敛的字体。)永善这样﹐永善那样。你的名字是可以这样随随便便道来的吗﹐即使是另一个名字﹑你的本名﹖你是个真实的人吗﹖对于我你还是一样遥远﹐你们都很远﹐而我像一个小孩子﹐在门后暗影里偷偷窥视大厅灯火中谈笑晏晏的大人﹐好想加入但知道那是没有可能的。去到西门町,多少次经过明星咖啡屋,知道你们这些人就在楼上,却鼓不起勇气上去与你们打招呼。我只有再一遍又一遍的阅读你。唯有从文字我可以熟识你﹐接近你﹐聆听你﹐甚至与你对话。在现实生活里我不能也不敢。
偶然我还是可以见到你的。 有一个晚上﹐干姐带我去看你﹐你领我们去淡水辉瑞药厂你的办公室取一样什么东西。那晚还有你的另一个陈姓朋友﹐后来跟你一起坐牢的。完全不记得你们说了些什么﹐或许真的没说什么。你的神色里有层层阴霾﹐我记得自己当时的直觉:这个人﹐这个我多么崇拜的遥不可及的小说家啊﹐这个人就在我面前﹐可是他似乎并不在这里﹐他总是若有所思﹐他的眼睛在注视关照着别的什么﹐像对着神秘而遥远的什么﹐他也有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吗﹖那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不论是什么样的﹐我将永远无法得知﹐永远﹑永远无法走近﹐甚至瞥见。我绝望地想。但我们到底还是在同一个房间里﹐那么近又那么远。我感到欣喜与微微的悲伤。
你远行前最后一次见到你是在台北火车站。我远远看见你独自站在那里像是在等候人﹐我的心默默的喊:是他是他真的是他﹗我犹疑着要不要上前打招呼﹐可是说什么呢﹐你若是不记得我怎么办﹐可是可是﹐这么难得啊﹐我可以单独与你说上几句话……我跟自己挣扎着﹐为难着﹐结果还是没有向你走去﹐不全是由于我的羞怯﹐而是你那时的神色。隔那么远也看出那沉郁和黯澹,像暴风雨来临的前夕。
果然。不久之后你和那些一起读书的人﹐包括我的干姐姐﹐都出事了。许多年后有一次我对你提起在火车站的那天﹐那段时日﹔你说是的﹐你记得那段日子﹐知道有些事情即将发生﹐你几乎在期待早些发生﹐因为等待那可怕时刻到来之前的时间是极其难过的。那是1968年。那一年里我经历了另一种成长:我这才发觉我对你知道的何其之少,你的文字里竟然还隐含那样巨大的危险与神秘。我再一次又一次细读你的小说,彷佛追寻你留给我和这个世间的密码。我想我读懂了。我无法忍受再留在这样一个密闭的地方,一个会监禁迫害你的地方。
去土城生教所探望过在那里服刑的干姐姐几次之后,我就出国了。这一离开,就是整整十五年。
如果不是你﹐1970年到了海外﹐我是否还会那样没有犹豫﹑没有迟疑﹑义无反顾的参加钓运统运﹖很难说。
你在牢狱中的岁月﹐我在海外轰轰烈烈的「保钓」年代里﹐如获至宝地读你的未及发表的旧作﹐还有偷偷流传出来的据说是新作。捧读着每一篇我都欣喜而悲伤的想﹕还好﹐他还在。虽然他还在苦难之中,但他还在世间,还在我们之中。
天哪你还在。1975年﹐谢谢天你终于平安出来了,而且立刻又提笔了。我读到你写你的父亲去监狱探视你时说的一段话﹐我让自己永远记住那段话。也是从那段时日﹐我给了开始写作的自己那样秘密的严格的要求 -
「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
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
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
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
我把这些话送给你﹐摆在羁旅的行囊中﹐据以为人﹐据以处事……」
你在其后加了这一段﹕「即使将『上帝』诠释成『真理』和『爱』﹐这三个标准都不是容易的。然而﹐唯其不容易﹐这些话才成为我一生的勉励。」
你的诠释将你我的「上帝」合一了 - 对我来说,我的「上帝」也正是对真理的尊重,从爱出发的人本的、终极的关怀。这是做人的次序 -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真正的「人」的次序。 有了那个「首先」,就不会昧于人事末节的纷争。我也以这些话作为自己一生的勉励,和为人处事的准则。
从1970年夏天离台赴美﹐直到1985年秋﹐台湾的政治气氛不再肃杀﹐我才能够在离国十五年之后回到台湾。1985﹐回想起来那是多么好的年代。白色已不再恐怖﹐人们试探着松弛的尺度。我终于见到你了﹐这次是真的见到了。那个曾经躲在门后窥视的小孩终于长大了﹐不再害羞胆怯﹐大大方方的走进来﹐走到你们的面前。然而昔日大厅里的一切都已改变﹐有些人已经不在﹐或已不复当年模样。你们没有等我长大就各自散了。所以我还是错过了,一个我没来得及赶上的时代﹐永远错过了。
我错过了【文季】年代的陈映真﹐不过还好﹐我没有错过【人间】杂志的陈映真。十五年后回到台湾,正逢1985年11月【人间】杂志创刊。台湾从未有过那样的刊物﹕强悍美丽而写实的黑白照片﹐对贫困﹑下层和弱势者人道关怀的故事﹔社会良知人权正义等等不再是空洞的文词﹐每一幅胜过千言万语的图像震撼着我们的眼睛。发刊词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这正是陈映真的话语﹐信望爱﹐上帝的孩子﹐却是全身全心的投注在人间,凡人的世间。那是台湾最可爱的年代。虽然世界离美好还很远﹐但充满了可能﹕关怀的可能﹐前行的可能﹐改变的可能。人性高贵的可能。不再有政治恐怖的可能……。【人间】杂志承载了那么多的可能。啊﹐还有﹐陈映真还会写出更多更好的小说的可能。
我真的以为这些「可能」大多实现了。多么美好的年代啊﹐我一生中第二次的纯真年代。
我因你而给了自己期许和检验﹐用你的标准﹐虽然你一无所知﹐我的感激是终生的。而我是多么孩子气啊﹐竟自以为几乎达到了你的标准。1986年我在台湾出版我的第一本小说集,你竟然答应我的要求为我写序!你竟然阅读我 - 在我阅读你二十多年后,你、竟然、阅读、我﹗更不会忘记1989年春天﹐在领一项文学奖的前夕﹐我向你预习领奖时的答词﹐你赞许的神色和言辞﹐是我心头对自我要求的天平上那块最后的﹑真正的砝码。你终于为我肯定了我自己。我一直、一直在等待你的那一块砝码啊。别的砝码都还不够﹐必须等待你的那一块放上﹐才算完成。长久以来我在等待你将我完成。
你哪里会知道这些﹐但有什么关系呢?何况在后进面前总是那样谦卑的你﹐我的感激的话语甚至可能会令你发窘的。而我还是那般天真﹐以为文学的路就是这样容易就走上了。
我重新认识你,在那个难忘的八○年代,不再仅只是通过文字,我认识了你这个人 - 在你那精炼华美得灼人的文字后面,竟然隐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稚朴。1987年你来到我当时居住的加州圣地亚哥,我陪你出门,在街上你见到穿着天主教神父装扮的人捧着募款箱,问也不问一声就投进一张大钞,动作快得令我来不及阻止。你说看见神父就想起韩国学生运动,神父们挺身站在正义的一边深深感动了你。我说神父化缘应当在教堂里,这些并无特别诉求而站在街头捧着纸箱要钱的人多半是骗子。你天真地驳问:他们若不是神父怎会穿着神父的衣袍?我硬着心肠告诉你:在任何一家化装派对店里都买得到假扮各类角色的装束,包括神父的衣领和黑袍。说完我就后悔了 - 你当时脸上诧异又无辜的表情令我不忍。我隐隐感到其实你是很容易受伤害的,因为你的心如此柔软,而且从不设防。
随着八○年代的结束﹐我的美好年代也结束在那时候﹕1989。而《人间》杂志也结束在那一年。
其后的写作﹐我很少再想着你的赞许了。事实上我已不在意来自任何人的赞许与否。我的生命中发生了大创伤,我与命运有无数艰难的死结要解。我的疗伤过程有不同的层次﹐我需要时间;而那年在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去思索,我们的那些关怀议题也显现不同的意义与距离。在心底我不再时时叩问你是否给我及格的分数﹐那些已经不再重要。也许,是到了我该从你的课室毕业的时候了。
但我在精神上从来不曾远离你。你依然是我的 mentor﹐每次见到你我仍然那样欣喜﹐仍然带着些微的感伤。每出一本书我依然不无紧张地呈上给你﹐是的每当面对你我还是像个交上作业的学生﹐那个剎那﹐我又是二三十年前那个羞怯的小孩﹐期待导师的微笑夸赞﹕「又出书了?好用功啊。」但我知道你多半不会细读的。你的关怀已远远超越文学之外﹐而我的书写主题也已与你的关怀重点不再全然密合。 但那只是中间层次距离的微小差异。至于那最根本和最崇高的﹐从来都没有需要去怀疑甚至重新确认 - 我从未怀疑过﹐因为它们从未改变过。
可是我还是多么期待你将你的关怀回头倾注在昔日那样的文学形式里,我深深怀念那些文字。我也知道你很难回头,昔日的文字形式无法承载你必须应答的急迫与焦虑。我要怎样才能说服你回去写出那些当年震撼我感动我的文字呢?学生怎么能够告诉导师他应该写甚么呢?我只能眼看你忙碌回应讥谗的冷箭,忍受中伤的苦痛,而健康江河日下⋯⋯
日前当我再一次回来这块我曾被你启蒙的土地,你却已经不在 - 这里甚至连你的栖身之处也没有了。回到这不再有你的城市里,我四顾茫然:到底发生了甚么事?我可以理解你曾经被一个忌恨你的庞大组织囚禁甚至杀戮,但我无法想象你竟会被一个你深爱的群体放逐。一个连你也容不下的地方,会是个甚么样的地方?
近年你日渐衰弱苍老。我习惯了文字不会衰弱苍老﹐以致常会忘却肉体会老去﹐虽然你的声音还是那样低沉优美﹐话语还是那样亲切温和 - 甚至更亲切更温和了﹐是由于你的衰弱乏力了吗?如果是,那简直令人心碎。对于一个我始终是仰望的人﹐我勉强能接受的是一头冬之狮。但是最后几次见到﹐我不能接受你已步入生命的冬日﹐而我甚至已见不到那头狮子……
但是我在说什么啊﹐你从来就不是狮子﹗你是一个温柔而谦卑的人﹐因为你记住自己是你的上帝的孩子﹐你的中国的孩子﹐你的父亲的孩子;不仅于此﹐你还是一个深爱你的女人的丈夫﹐一个写作的人 - 写作的人﹐是的﹐一切从文字开始﹕你给予我的启蒙﹐我的感动﹐我的认知。你让我懂得什么是心灵的高贵﹐对我证明文字的优美魅丽与思维义理可以并存 - 毫无冲突的和谐融会的并存。是你给了我青春岁月里无悔的理想与追寻﹐我心甘情愿加诸自身的要求和期许﹐你示范给我看到最诚实最优美又最雄辩的文字﹐虽然你并不知道但是你始终在教我写作 - 是的我的写作﹐我的从不妥协﹑从不须自欺更不会欺人的写作。
对照你是谁的孩子当我自问我自己是谁的孩子﹐我毫无犹疑的如同你的肯定的答案﹕你的上帝和我的上帝原是同一﹐原是那个让你无悔奉献的终极真理﹔所以你一直不曾远离我﹐因为我不会让你远离﹐因为我从未改变过我是谁﹑我是谁的孩子的答案。
你是我终生的 mentor。从来都是﹐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你从不曾从你的信仰﹑希望和关爱改变。
(2009年8月26日,美国加州史丹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