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
- 小说
- 艺术
- 古籍善本(国学)
- 动漫绘本
- 生活
- 励志
- 社科
- 经管
- 文化
- 教育
- 幼儿读物
- 体育
- 外语
- 历史
- 地理
- 计算机
- 科技
- 生物
- 医学
- 农林
- 工业
- 综合
- 进口原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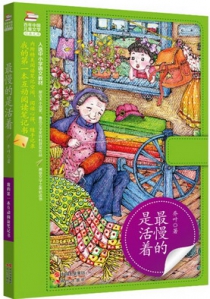
-
一个大字不识、独自一人拉扯着全家老小,一辈子也不愿离开故土的农村老太太,是我的祖母; 一个命硬脾气也硬,从小叛逆、不甘寂寞,年轻轻的便走南闯北,历尽世事的女孩,是我。 她从小便不喜欢我,我也因此不喜欢她...
一个大字不识、独自一人拉扯着全家老小,一辈子也不愿离开故土的农村老太太,是我的祖母;
一个命硬脾气也硬,从小叛逆、不甘寂寞,年轻轻的便走南闯北,历尽世事的女孩,是我。
她从小便不喜欢我,我也因此不喜欢她,兄妹四个中,就我相貌极肖她,可就我和她不对路。
是怎样的磕磕绊绊,让我逐渐悟出:“不喜欢”,是她送给我最初的精神礼物?
是怎样的血浓于水,让我选择一直留在她的身边,静静地陪着她,送走父亲,送走母亲,经历兄弟姐妹的人生变故......直至送走她?
是怎样的时空距离,使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和她,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活着这件原本最快的事,也因此,变成了最慢。
一、最慢的是活着
二、爆米花
三、家常话
四、语文课
五、指甲花开
1
那一天,窗外下着不紧不慢的雨,我和朋友在一家茶馆里聊天,不知怎的,她聊起了她的祖母。她说她的祖母非常节俭。从小到大,她只记得祖母有七双鞋:两双厚棉鞋冬天里穿,两双厚布鞋春秋天穿,两双薄布鞋夏天里穿,还有一双是桐油油过的高帮鞋,专门雨雪天里穿。小时候,若是放学早,她就负责烧火。只要灶里的火苗窜到了灶外,就会挨奶奶的骂,让她把火压到灶里去,说火焰扑棱出来就是浪费。
“她去世快二十年了。”她说。
“要是她还活着,知道我们这么花着百把块钱在外面买水说闲话,肯定会生气的吧?”
“肯定的,”朋友笑了,“她是那种在农村大小便的时候都会去自家地里的人。”
我们一起笑了。我想起了我的祖母——这表述不准确,也许还是用她自己的话来形容才最为贴切:“不用想,也忘不掉。钉子进了墙,锈也锈到里头了。”
我的祖母王兰英,一九二○年生于豫北一个名叫焦作的小城。焦作盛产煤,那时候便有很多有本事的人私营煤窑。我曾祖父在一个大煤窑当账房先生,家里的日子便很过得去。一个偶然的机会,曾祖父认识了祖母的父亲,便许下了媒约。祖母十六岁那年,嫁到了焦作城南十里之外的杨庄。杨庄这个村落由此成为我最详细的籍贯地址,也成为祖母最终的葬身之地。二○○二年十一月,她病逝在这里。
2
我一共四个兄弟姊妹,性别排序是:男、女、男、女。大名依次是小强、小丽、小杰、小让。家常称呼是大宝、大妞、二宝、二妞。我就是二妞李小让。小让这个名字虽是最一般不过的,却是四个孩子里唯一花了钱的。因为命硬。乡间说法:命有软硬之分,生在初一、十五的人命够硬,但最硬的是生在二十。“初一十五不算硬,生到二十硬似钉。”我生于阴历七月二十,命就硬得似钉了。为了让我这钉软一些,妈妈说,我生下来的当天奶奶便请了个风水先生给我看了看,风水先生说最简便的做法就是在名字上做个手脚,好给老天爷打个马虎眼,让他饶过我这个孽障,从此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于是就给我取了让字。在我们方言里,让不仅有避让的意思,还有柔软的意思。
“花了五毛钱呢。”奶奶说,“够买两斤鸡蛋的了。”
“你又不是为了我好。还不是怕我妨了谁克了谁!”
这么说话的时候我已经上了小学,和她顶嘴早成了家常便饭。这顶嘴不是撒娇撒痴的那种,而是真真的水火不容。因为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当然,身为弱势,我的选择是被动的:她先不喜欢我,我也只好不喜欢她。
亲人之间的不喜欢是很奇怪的一种感觉。因为在一个屋檐下,再不喜欢也得经常相见,所以自然而然会有一种温暖。尤其是大风大雨的夜,我和她一起躺在西里间,虽然各睡一张床,然而听着她的呼吸,就觉得踏实,安恬。但又因为确实不喜欢,这低凹的温暖中就又有一种高凸的冷漠。在人口众多川流不息的白天,那种冷漠引起的嫌恶,几乎让我们不能对视。
从一开始有记忆起,就知道她是不喜欢我的。有句俗语:“老大娇,老末娇,就是别生半中腰。”但是,作为老末的我却没有得到过她的半点娇宠。她是家里的慈禧太后,她不娇宠,爸爸妈妈也就不会娇宠,就是想娇宠也没时间,爸爸在焦作矿务局上班,妈妈是村小的民办教师,都忙着呢。
因为不被喜欢,小心眼儿里就很记仇。而她让我记仇的细节简直是俯拾皆是。比如她常睡的那张水曲柳木黄漆大床。那张床是清朝电视剧里常见的那种大木床,四周镶着木围板,木板上雕着牡丹、荷花、秋菊、冬梅四季花式。另有高高的木顶,顶上同样有花式。床头和床尾还各嵌着一个放鞋子的暗柜,几乎是我家最华丽的家具。我非常向往那张大床,却始终没有在上面睡的机会。她只带二哥一起睡那张大床。和二哥只间隔三岁,在这张床的待遇上却如此悬殊,我很不平。一天晚上,便先斩后奏,好好地洗了脚,早早地爬了上去。她一看见就着了急,把被子一掀,厉声道:“下来!”
我缩在床角,说:“我占不了什么地方的,奶奶。”
“那也不中!”
“我只和你睡一次。”
“不中!”
她是那么坚决。被她如此坚决地排斥着,对自尊心是一种很大的伤害。我哭了。她去拽我,我抓着床栏,坚持着,死活不下。她实在没有办法,就抱着二哥睡到了我的小床上。那一晚,我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占着那张大床。我是在泪水中睡去的,清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接着哭。
她毫不掩饰自己对男孩子的喜爱。谁家生了儿子,她就说:“添人了。”若是生了女儿,她就说:“是个闺女。”儿子是人,闺女就只是闺女。闺女不是人。当然,如果哪家娶了媳妇,她也会说:“进人了。”——这一家的闺女成了那一家的媳妇,才算是人。因此,自己家的闺女只有到了别人家当媳妇才算人,在自己家是不算人的。这个理儿,她认得真真儿的。每次过小年的时候看她给灶王爷上供,我听的最多的就是那一套:“……您老好话多说,赖话少言。有句要紧话可得给送子娘娘传,让她多给骑马射箭的,少给穿针引线的。”骑马射箭的,就是男孩。穿针引线的,就是女孩。在她的意识里,儿子再多也不多,闺女呢,就是一门儿贴心的亲戚,有事没事走动走动,百年升天脚蹬莲花的时候有这把手给自己梳头净面,就够了。因此再多一个就是多余——我就是最典型的多余。她原本指望我是个男孩子的,我的来临让她失望透顶:一个不争气的女孩身子,不仅占了男孩的名额,还占了个男孩子的秉性,命还那么硬。她怎么能够待见我?
做错了事,她对男孩和女孩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要是大哥和二哥做错了事,她一句重话也不许爸爸妈妈说,且原因充分:饭前不许说,因为快吃饭了;饭时不许说,因为正在吃饭;饭后不许说,因为刚刚吃过饭;刚放学不许说,因为要做作业;睡觉前不许说,因为要睡觉……但对女孩,什么时候打骂都无关紧要。她就常在饭桌上教训我的左撇子。我自会拿筷子以来就是个左撇子,干什么都喜欢用左手。平时她看不见就算了,只要一坐到饭桌上,她就要开始管教我。怕我影响大哥、二哥和姐姐吃饭,把我从这个桌角撵到那个桌角,又从那个桌角撵到这个桌角,总之怎么看我都不顺眼,我坐到哪里都碍事儿。最后通常还是得她坐到我的左边。当我终于坐定,开始吃饭,她的另一项程序就开始了。
啪!她的筷子敲到了我左手背的指关节上,生疼生疼。
“换手!”她说,“叫你改,你就不改。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不会。”
“不会就学。别的不学这个也得学!”
知道再和她犟下去,菜就被哥哥姐姐们夹完了,我就只好换过来。我鼓嘟着嘴巴,用右手生疏地夹起一片冬瓜,冬瓜无声无息地落在饭桌上。我又艰难地夹起一根南瓜丝,还是落在了饭桌上。当我终于把一根最粗的萝卜条成功地夹到嘴边时,萝卜条却突然落在了粥碗里,粥汁儿溅到了我的脸上和衣服上,引得哥哥姐姐们一阵嬉笑。
“不管用哪只手吃饭,吃到嘴里就中了,什么要紧。”妈妈终于说话了。
“那怎么会一样?将来怎么找婆家?”
“我长大就不找婆家。”我连忙说。
“不找婆家?娘家还养你一辈子哩?还给你扎个老闺女坟哩?”
“我自己养活自己,不要你们养。”
“不要我们养,你自己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自己给自己喂奶长这么大?”她开始不讲逻辑,我知道无力和她抗争下去,只好不作声。
下一次,依然如此,我就换个花样回应她:“不用你操心,我不会嫁个也是左撇子的人?我不信这世上只我一个人是左撇子!”
她被气笑了:“这么小的闺女就说找婆家,不知道羞!”
“是你先说的。”
“哦,是我先说的。咦——还就我能先说,你还就不能说。”她得意扬扬。
“姊妹四个里头,就你的相貌极肖她,还就你和她不对路。”妈妈很纳闷,“怪哩。”
3
后来听她和姐姐聊天我才知道,她小时候娘家的家境很好,那时我们李家的光景虽然不错,和她们王家却是绝不能比的。他们大家族枝枝杈杈四五辈,共有四五十口人,男人们多,家里还雇有十几个长工,女人们便不用下地,只是轮流在家做饭。她们这一茬女孩子有八九个,从小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是学做女红和厨艺。家里开着方圆十几里最大的磨坊和粉坊,养着五六头大牲口和几十头猪。农闲的时候,磨房磨面,粉坊出粉条,牲口们都派上了用场,猪也有了下脚料吃,猪粪再起了去壮地,一样也不耽搁。到了赶集的日子,她们的爷爷会驾着马车,带她们去逛一圈,买些花布、头绳,再给她们每人买个烧饼和一碗羊杂碎。家里哪位堂哥娶了新媳妇,她们会瞒着长辈们偷偷地去听房,当然也常常会被发现。一听见爷爷的咳嗽声,她们就会作鸟兽散,有一次,她撒丫子跑的时候,被一块砖头绊倒,磕了碗大的一片黑青。
嫁过来的时候,因为知道婆家这边不如娘家,怕姑娘受苦,她的嫁妆就格外丰厚:带镜子和小抽屉的脸盆架、雕花的衣架、红漆四屉的首饰盒、一张八仙桌、一对太师椅、两个带鞋柜的大樟木箱子、八床缎子面棉被……还有那张水曲柳的黄漆木床。
“一共有二十抬呢。”她说。那时候的嫁妆是论“抬”的。小件的两个人抬一样,大件的四个人抬一样。能有二十抬,确实很有规模。
说到兴起,她就会打开樟木箱子,给姐姐看她新婚时的红棉裤。隔着几十年的光阴,棉裤的颜色依然很鲜艳。大红底儿上印着淡蓝色的小花,既喜悦,又沉静。还有她的首饰。“文革”时被“破四旧”的人抢走了许多,不过她还是偷偷地保留了一些。她打开一层层的红布包,给姐姐看:两只长长的凤头银钗,因为时日久远,银都灰暗了。她说原本还有一对雕龙画凤的银镯子,三年困难时期,她响应国家号召向灾区捐献物资,狠狠心把那对镯子捐了。后来发现戴在了一名村干部女儿的手上。
“我把她叫到咱家,哄她洗手吃馍,又把镯子拿了回来。他们到底理亏,没敢朝我再要。”
“那镯子呢?”
“卖了,换了二十斤黄豆。”
她生爸爸的时候,娘家人给她庆满月送的银锁,每一把都有三两重,一尺长,都佩着烦烦琐琐的银铃和胖胖的小银人儿。她说原先一共有七把,“破四旧”时,被抢走了四把,就只剩下了三把,后来大哥和二哥生孩子,生的都是儿子,她就一家给了一把。姐姐生的是女儿,她就没给。
“你再生,要生出来儿子我就给你。”她对姐姐说,又把脸转向我,“看你们谁有本事先生出儿子。迟早是你们的。”
“得了吧。我不要。”我道,“明知道我最小,结婚最晚。根本就是不存心给我。”
“你说得没错,不是给你的,是给我重外孙子的。”她又小心翼翼地裹起来,“你们要是都生了儿子,就把这个锁回回炉,做两个小的,一人一个。”
偶尔,她也会跟姐姐聊起祖父。
“我比人家大三岁。女大三,抱金砖。”她说,她总用“人家”这个词来代指祖父。“我过门不多时,就乱了,煤窑厂子都关了,你太爷爷就回家闲了,家里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啥金砖?银砖也没抱上,抱的都是土坷垃。”
“人家话不多。
“就见过一面,连人家的脸都没敢看清,就嫁给人家了。那时候嫁人,谁不是晕着头嫁呢?
“和人家过了三年,哪年都没空肚子,前两个都是四六风 。可惜的,都是男孩儿呢。刚生下来的时候还好好儿的,都是在第六天头上死了,要是早知道把剪刀在火上烤烤再剪脐带就中,哪会只剩下你爸爸一个人?”
后来,“人家”当兵走了。
“八路军过来的时候,人家上了扫盲班,学认字。人家脑子灵,学得快……不过,世上的事谁说得准呢?要是笨点儿,说不定也不会跟着队伍走,现在还能活着呢。”
“哪个人傻了想去当兵?队伍来了,不当不行了。”她毫不掩饰祖父当时的思想落后,“就是不跟着这帮人走,还有国民党呢,还有杂牌军呢,哪帮人都饶不了。还有老日呢。”——老日,就是日本鬼子。
“老日开始不杀人的。进屋见了咱家供的菩萨,就赶忙跪下磕头。看见小孩子还给糖吃,后来就不中了,见人就杀。还把周岁大的孩子挑到刺刀尖儿上耍,那哪还能叫人?”
老日来的时候,她的脸上都是抹着锅黑的。
“人家”打徐州的时候,她去看他,要过黄河,黄河上的桥散了,只剩下了个铁架子。白天不敢过,只能晚上过。她就带着爸爸,一步一步地踩过了那条漫长的铁架子,过了黄河。
“月亮可白。就是黄河水在脚底下,哗啦啦地吓人。”
“人家那时候已经有通讯员了,部队上的人对我们可好。吃得也可好,可饱。住了两天,我们就回来了。家属不能多住,看看就中了。”
那次探亲回来,她又怀了孕,生下了一个女儿。女儿白白胖胖,面如满月,特别爱笑。但是,一次,一个街坊举起孩子逗着玩的时候,失手摔到了地上。第二天,这个孩子就夭折了,才五个月。
讲这件事时,我和她坐在大门楼下。那个街坊正缓缓走过,还和她打着招呼。
“歇着呢?”
“歇着呢。”她和和气气地答应。
“不要理他!”我气恼她无原则的大度。
“那还能怎么着?账哪能算得那么清?他也不是蓄心的。”她叹气,“死了的人死了,活着的人还得活着。”
后来,她收到了祖父的阵亡通知书。“就知道了,人没了。那个人,没了。”
“听爸爸说,解放后你去找过爷爷一次。没找到,就回来了。回来时还生了一场大病。”
“哦。”她说,“一个人说没就没了,一张纸就说这个人没了,总觉得不真。去找了一趟,就死心了。”
“你是哪一年去的?”
“五六年吧。五六、五七,记不清了。”
“那一趟,你走到了哪儿?”
“谁知道走到了哪儿。我一个大字不识的妇女,到外头知道个啥。”
……







